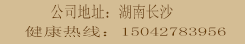三
她拿裁纸刀在玻璃上划过,然后把它那光滑而冰凉的表面贴在她的脸颊上,出于突然间无端地攫住她的快乐,她差点儿笑出声我来。
???????????????《安娜·卡列尼娜》(1·29)
1,传庆掉过头去不言语,把脸贴在玻璃上。他不能老是凑在她跟前,用全副精神听她说话。让人瞧见了,准得产生某种误会。说闲话的人已经不少了,就是因为言丹朱总是找着他。在学校里,谁都不理他。他自己觉得不得人心,越发的避着人,可是他躲不了丹朱。
2,她走了,传庆把头靠在玻璃窗上,又仿佛盹着了似的。前面站着的抱着杜鹃花的人也下去了,窗外少了杜鹃花,只剩下灰色的街。他的脸换了一幅背景,也似乎是黄了,暗了。???????????
3,他夹了书向下跑,满心的烦躁。客室里有着淡淡的太阳与灰尘。霁红花瓶里插着鸡毛帚子。他在正中的红木方桌旁边坐下,伏在大理石桌面上。桌面冰凉的,像公共汽车上的玻璃窗。
窗外的杜鹃花,窗里的言丹朱……丹朱的父亲是言子夜。那名字,他小时候,还不大识字,就见到了。在一本破旧的《早潮》杂志封里的空页上,他曾经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认着:“碧落女史清玩。言子夜赠。”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冯碧落。
???????????????????张爱玲《茉莉香片》
让我们进行一次纳博科夫式的细读。在第一部第二十九章伊始,安娜坐到了回彼得堡的火?上,“‘好了,一切都结束了,感谢上帝!’这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同第三次响铃后仍挡在车厢过道上的哥哥最后一次告别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好了,一切都结束了”意味着小说以稳态开始,安娜希望回到车厢意味着莫斯科与弗隆斯基风波的结束,车厢内“一位生病的太太已经躺下睡觉。其他两位太太跟她聊了起来,肥胖的老太太把脚包起来,对火炉表示了意见。安娜对几位太太应答了几句,但没看出这种谈话有什么意思,便让安奴什卡拿出小提灯,把它挂在椅子的扶手上,从自己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文小说。”车厢内的世界并没什么意思,(关于火车意象有很多解读,笔者赞同火车即社会说:火车在《安娜》中象征了现实社会,它不仅让安娜遇到了弗隆斯基,也杀了安娜)安娜从她的红色手提包中(令人想起潘多拉或者普绪克的盒子,红色手提包也是《安娜》火车意象组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和安娜农夫之梦的袋子мешок一脉相承,有论者认为具有子宫的象征意义。)取出裁纸刀,用刀裁开那本毛边的英文小说,进入了小说世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理解着,但她读得不愉快,也就是在追随着别人生活的影子。她过于想自己去生活了。她读到小说中的女主?照顾病人,她就想迈着悄无声息的步子走在病人的房间里;她读到议会成员发言,便想做这番发言;她读到梅丽小姐骑?去狩猎,戏弄嫂嫂,以自己的勇敢震惊众人时,她就想自己也这样做。然而却没什么事可做,而她,只是用自己小巧的双手摆弄着光滑的小刀,勉强读下去。”小说在小说中意味着什么?从《唐·吉诃德》到《包法利夫人》——脱离了现实世界之重的另一个世界(这一点我们将在笔记5中做更详尽的分析。)随后安娜回忆起了彼得堡发生的事情:“就在她回忆起弗隆斯基时,对她说:‘暖和,很暖和,热啊。’......她轻蔑地笑了,又拿起书,但已经完全无法明白读的是什么了。她拿裁纸刀在玻璃上划过,然后把它那光滑而冰凉的表面贴在她的脸颊上,出于突然间无端地攫住她的快乐,她差点儿笑出声来。”热与冷,车厢里热得难受,安娜需要裁纸刀/玻璃降降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实世界-小说世界和?厢里的世界-窗外的世界的对应关系,通过裁纸刀划窗和脸贴玻璃两个动作,裁纸刀与玻璃窗间完成了微妙的转化,冰冷的裁纸刀切开了小说,冰冷的窗户外展开了新的世界,?厢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太热,难以忍受,要到窗外的世界(小说世界)去:风雪,无限的激情和弗隆斯基等在那里。随后,“她感觉到,她的神经就像某种旋动的木栓上越绷越紧的弦线。她感觉到,她的眼睛越睁越大,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抖动着,胸口有什么东?压迫着呼吸,在这晃动不定的昏暗中所有形象和声音以不同寻常的清晰令她惊讶。”接着是梦魇般的幻觉(农夫/乡下人「мужик」之梦的第一次预演):“这个腰身??的乡下人去啃墙上的什么东?,老太太开始把她的腿伸到整个?厢那么?,让?厢充满乌云;接着什么东?可怕地发出吱吱嘎嘎和敲打的声响,好像什么人被碾碎了;然后是令人目眩的红色火光,然后一切都被墙壁遮住了。”这也是安娜之死的预演。到达了莫斯科与彼得堡间的中点站,“‘您要出去吗?’安奴什卡问道。‘是的,我想喘口气。这里太热了。’她打开?。雪暴和?朝她猛扑过来,开始跟她抢夺??。这样让她觉得很愉快。她打开门走了出去。风仿佛就在等着她,高兴地吹着呼哨,想把她抓起来带走,但她用有力的手抓紧冰冷的柱子,按住衣服,下车来到月台上,朝车厢后面走去。风在梯级上很猛,在月台上的车厢背后就平静了。她满怀愉悦,足足地吸入那清新、寒冷的空气,站在车厢旁边,环视着月台和灯火明亮的车站。”安娜在这里遇到了弗隆斯基。
而在张爱玲的《茉莉香片》中,恰恰相反,寒冷代表的不是交通人心的激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张腔所独有的),玻璃不是通向新世界的窗户,而是堵塞他人走入自我之路的坚冰。
我们可以从小说整体中把握所引的玻璃细节。小说中聂传庆的稳态共被打破两次,我们知道,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打破稳态是探索人物内心的重要手段(可以和廉价的好莱坞电影们作比,外星人入侵或者地球的倾覆都只是为了成就主角一家的二世同堂,恢复片初的温馨生活。)分别如下:
一,公交车,聂传庆遇到言丹朱。(稳态)
二,聂传庆发现自己的老师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夜是母亲的初恋。(打破稳态)
三,聂传庆想象“如果”母亲勇敢地与言子夜私奔,那么自己就可以成长在完全另一个、更好的家庭中,像言丹朱一样,甚至比她更好。(稳态)
四,聂传庆被言子夜怒斥,与生父并无不同。(打破稳态)
五,聂传庆的幻想既然破灭,幻想通过与言丹朱结婚获得亲情的爱,不得,殴打言丹朱。(新常态)
前文所引段1在第一阶段,段2在第二阶段,段3在第三阶段。在小说一开始我们知道,聂传庆的前面站着一个抱着一大捆牡丹花的人,“人倚在窗口,那枝枝桠桠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这一场景也十分极富视觉化效果,纳博科夫也许会让学生画出这一场景的平面示意图。)段1中的聂传庆是最初稳态中的聂传庆,忧郁但不绝望,言丹朱上来了,杜鹃花虽隔着窗户,毕竟还火红着(丹朱-火红的杜鹃花。我们会发现在张爱玲早期关于香港的三篇作品中均出现了杜鹃花。)在段2中,聂传庆被打破了稳态,言丹朱下了车,窗外杜鹃花没了。段3中言丹朱却被聂传庆的意识投射到了窗内,这也许是聂传庆幻想自己“如果”成为言丹朱的暗示与先声,然而火红的杜鹃花仍在窗外,他终究不是言丹朱。
4
“露出牙齿”这一动作在整部小说中出现过15次,属于弗隆斯基的有8次,属于卡列宁的有2次,谢尔巴茨基家的家庭女教师M-lleLinon1次,骑手马霍金1次,瓦莲卡1次,写生画家彼得洛夫1次,卡塔瓦索夫1次。
大家知道,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一般会有一些核心特征,譬如丽莎公爵夫人的唇髭,卡列宁扳响手指的习惯等,而弗隆斯基的核心特征是他那结实的(крепкие)整齐的(сплошные)洁白的(белые)牙齿。
这是塑造人物形象层面的技巧,但在进一步阅读后会发现,牙齿是将弗隆斯基、卡列宁、列文连接起来的意象之一。托尔斯泰在谈及《安娜》时曾指出其中有一个“无尽的迷宫之链”(бесконечныйлабиринтсцеплений),牙齿意象也许是其中的线索之一。现罗列如下:
1,每过一个星期他就更少想起吉蒂。他焦急地期待着她已经出嫁或者近日就要出嫁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就像拔牙一样,彻底将他治愈。
与此同时春天来了,可爱、友善,不必久待,也没有春天的种种欺骗,这是一个罕有的春天,令草木、动物和人同样欢喜。这可爱的春天更加激励了列文,让他定下信念摒弃过去的一切,以便牢固而独立地安排自己的单身生活。(2·12)
2,他体会到一个人拔掉疼了很久的牙齿的心情,经受了可怕的疼痛和某种巨大的、大过脑袋本身的东西拔出颌骨的感觉之后,病人突然之间,都不相信自己的幸福,感到那样久久地毒害了他生活、禁锢了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不复存在,感到他又能生活、思考,不仅仅只关心一颗牙齿的事情了。这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体会到的感觉。那疼痛奇怪而又可怕,但现在它已经过去了;他觉得他又能生活下去,不必只想着妻子了。(3·13)
3,但是,无论他如何盘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能不能不做圣餐祈祷便获得证明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宣称这是不可能的。
“可这又能占去你多少时间——两天?而且他是个很可亲又聪明的老头儿。他给你把这颗牙拔了,你都注意不到。”(5·1)
4,突然间一种全然不同的,不是疼痛,而是泛泛地折磨人的内在窘迫使他瞬间忘记了牙疼。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受到与自己发生不幸后还没有见过面的这位熟人交谈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也就是所余下的那部分她,那时他,就像疯子似的冲进铁路车站的工房:工房的桌子上,不久之前还充满生命活力的血淋淋的躯体,毫无羞耻地在一堆生人中间横陈着。向后仰着的完好的头部,带着沉甸甸的发辫和鬓角处的鬈发,而在那张绝美的脸上,半张着的绯红的嘴巴,凝固出嘴角上奇怪、可怜、在那双一动不动、未能闭合的眼睛里令人惊惧的表情,就像用言语说出那句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那是她在争吵时对他说的话。
他竭力回想着当时的她,他第一次遇见她也是在火车站,她神秘、美妙迷人、富于爱意,找寻并给予着快乐,而不是残忍地想要报复——她让他不觉回想起的最后一刻的样子。他竭力回想着与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刻,但这些时刻永远地被毒化了。他只记住了得意洋洋、实现了谁都不需要的威胁的她,其悔意却难以消除。他不再感觉牙疼,一阵悲咽扭曲了他的脸。(8·5)
以上所举四段中,两段为列文,一段为卡列宁,最后一段为弗隆斯基,列文与卡列宁都是拔牙之喻,弗隆斯基则是牙疼,纳博科夫对第一部分的注一零四中说:“当弗隆斯基在小说第八部分的书页上消失时,他的创造者为了惩罚他的出众体格,让他遭受了牙疼之苦,描写精彩之极。”我们认为这仍然没有注意到牙齿在整部小说中勾连人物和象征的作用。
从卡列宁入手,这是年8月注安娜在从赛马场画家的路上向卡列宁坦白自己与弗隆斯基关系后的心理描写:感到一颗疼了很久的牙被拔了,随后又是个比喻:仿佛一个比脑袋更大的东西被拔了出来。这是个大巧若拙的比喻,一个长久的累赘被卸去了,但这样的卸去有甚于斩首之痛者。在此之后卡列宁仍?久处于痛苦的挣扎中,但在安娜生产的那个晚上展示了圣人般的宽恕的力??量。
其次是列文,第1段发生于列文第一次求婚失败回到乡间后,第3段则来自于列文第二次求婚成功,奥勃朗斯基建议列文去教堂领圣餐语,两段恰为照应。
最后是弗隆斯基,如13段所述,在这里牙疼的缓解与拔牙的感受类似,由火?旧景勾起的对安娜的回忆展示出了救赎的力量,因为安娜之死而带来的牙痛的惩罚(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轻微了些),最终得到了宽恕。
综上所述,三个人的四段与牙?有关的心灵转折各有其背景,但均是走向自我救赎的转折点。与《旧约·申命记》“以牙还牙”的说法相反相成,牙?在小说中仿佛是上帝审判世人的工具,正如小说中所说:“将要审判他们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6·20)
注:笔记6将会涉及小说系年,纳博科夫认为小说开始于年,笔者一开始也同意这个说法,但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在第一部到第四部之间,安娜时间组度过了两年,而列文时间组只度过了一年,而在第四部开头两个时间组第二次相遇,给系年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最好从后往前计算时间,毕竟结尾年夏天是确定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kataera.com/krwh/58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