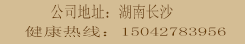最近又有出版社新出了张爱玲的《少帅》,这是张在落魄时写成的一部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这几年,张爱玲热一直只增不减,各种版本的相关书目更是像挤牙膏一样,时不时就冒出来。有人说她的作品登不得大雅之堂,因为她的作品不是主流文学要求的那样,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紧密与时代相连,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她的作品只是“入世近俗,执着于饮食男女,吃穿用度,身边琐事。”像是更高级精致的“鸳蝴派小说”,但爱她的人,偏偏就是着迷,浅者得其浅,深者自觉其深。但谁也不能否认,她对人性独到的、稳定地把握,相当圆熟的技巧,以及臻于佳境的文字。这些放诸现代文学史,再无二人。
我读过各式各样有关张爱玲的文字,除了这种正式的传记,还不乏各式汇编成册的“民国女子”系列,但凡有她的名字,我必如从未接触过一般捧来细读。其状恰如本次我想与大家分享的这本由余斌写成的《张爱玲传》开篇引言所述:“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对她的书是真的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他们莫大的快感。”下面,我将结合这本优秀的传记作品,以及我本人对张爱玲的理解,在这段难得的属于我和张爱玲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将一个传奇一样的她向大家展示出来,同时,也把我读这本传记时学到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
(一)从前的生活“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只是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地想到历史。”由此我最先谈她的家庭。
余斌所著这本传记能在十多年里重印多次,必有他优秀之处,他告诉我,写人物传记的第一点,即所有出现的人物,不论他们有多少故事,他们都是要为传主服务的。这使得在描述张家庭中的人物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对他们做出公允地评价,而是叙述他们在传主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的举措对传主的心理有何影响,以及传主对他们的复杂态度。
张的出身可谓名门望族,祖父张佩纶乃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外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作品中对于一些微妙的感受的追述十分纤细,有工笔画的风致,她能在作品中提供有关房屋、室内陈设、服饰等大量的细节描绘,这与她当年的贵族生活和那种环境下养成的精致纤巧的趣味有直接关系。她的家中也弥漫着文学的空气,私塾教育、读古书、作旧诗,这些都间接培养了她的古典文学素养。
然而这样显赫的出身,张家的后人难做,于是后人很快就变成了贵族遗少。张的父亲虽前期对她宠爱有加,后期就开始吸食鸦片,迎娶的后母又施虐于张,导致她只好夜里逃离去往生母去处。生母又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对亲情向来淡漠,关心的只有如何将张培养成一个淑女。她并不关心张在写作上展露的才华,只看到她在应付人情世故时的窘态与笨拙。这不利的生活环境给予她性格发展有了一个共同地指向:朝着内省、敏感与自我封闭的路上走,孤独与寂寞不可避免地成了她早年生活最重大的情感体验。也是这种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张在日后选择人生伴侣时,总是在极大地寻求安全感,这也为她两次悲剧的婚姻埋下了种子。
(二)读书岁月与港战印象这里我要提到余斌在这本传记中告诉我的第二点,即写传主的近乎琐碎的生活的用处。因为传主本人是一个作家,所以她的日常生活和所见所闻和她本人的创作间必然存在联系,这并不是要做索引,而是帮助我们去感知她的经验世界与小说整体之间的对应。
张投奔生母后,便一直在教会女校学习,这期间的学习帮助她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后来她又到香港留学,那时的香港对于张来说是全新的天地,殖民地怪异的风俗人情,接近热带的奇异地理自然环境,给她留下了新鲜、深刻的印象。她的成名作《沉香屑》即是关于香港的“传奇”,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港战”这一事件对于张人生观及创作风格的直接影响。战事使张得到了一次直接与社会照面的机会,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为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个人性的内容,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是那样不可捉摸、无从控制,她的不安之感越发强烈。她深切地明白了,个人世界的安稳在惊天动的变革面前,有多么地难以守护。因此,她的小说尽管大多不是社会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闭世界的浑然不觉的人物的视界之外,我们可以隐约意识到故事的后面,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
下面为大家朗读一段节选自《烬余录》结尾的话,让我们看到张是怎样带着难以明言的复杂情绪去接受她在战争中发现的真相的: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长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孤独的。”
(三)《传奇》世界余斌通过这本传记告诉我的第三点,如果传主是作家,分析其作品应当是最重要的任务。本书几近2/3的内容都是在分析或者评论张的作品的。这也是这本传记不同于我之前读过的书的一大特点,之前的传记总是在描写或者想象张的生活,很少从她的作品中做深入地挖掘。
从《天才梦》发表以后,张爱玲三年没有动笔。直到从香港归来,再拿起笔的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多了几分自信,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
张回到上海后,从第一次在《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而她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也在这段时间相继问世。那就是《传奇》勾画的世界。
不知在座各位有没有看过张的作品,她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没有一个是写英雄人物。她要取消英雄主义,书名虽是《传奇》,可目的是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并不像当时批评她的傅雷先生一样迷恋悲剧的崇高,推崇英雄气概。张描写的总是些“软弱的凡人”。在《传奇》世界中,人物都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很多人仿佛忘却了时代,始终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这些病态人物凑在一起,反映的是身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的病态,张爱玲准确地把握了这些人物封闭其中的颓丧和没落。这也与她本人是没落世家的后裔有巨大联系。
《传奇》中的人物登场时,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抱着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以为自己的处境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善,然而当故事迎来结局,他们的信念全部夭折,不得不承认现实与环境的力量。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在开场时是坚信自己可以维护人格的完整的,结果最后也只是做了乔其乔的情妇。人逃脱不了情欲的支配,这是张对人性的规定。
另外,《传奇》中的意象之丰富,也非常值得一提。《金锁记》中最著名的关于月亮的描写:“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这些新颖的描摹背后是作者本人活泼的直觉,读起来还有电影镜头的转移感。意象点化的隐喻手法,和对象征的追求,这本是西方小说的传统,而张本身的文字又极具古典风格,这种新旧的糅合,构成了张小说独特的风貌。
(四)一语成谶的爱情悲剧余斌在这本传记作品中告诉我的第四点,即要对有关传主的详细材料的充分占有。余斌可谓在这方面下了苦力,张本人是对个人生活素少谈论的,晚年更是不欲引起公众注意,牢守“私家重地,请勿践踏”的态度。然而余斌还是通过各种书信,他人的记载来搜寻蛛丝马迹,并且对张的所有文章进行熟读,加以分析,难得的将张移民美国之后的生活也描绘了许多。
提到张的爱情,不得不提那个可谓文如其人,大言不惭,沾沾自得的汉奸胡兰成。胡是读到那篇《封锁》后有了想结识张的愿望的,他颇有一些旧文人的风流自赏,因此多才子配佳人的绮思,而且张出身名门,家世背景也令贫儿暴富的胡兰成觉得脸上有光。尽管写下了那么多爱情名篇,张本人却是没有一点爱情经历,而胡在没有经验的女子面前常常是从容自信,若即若离的撩拨是他惯用的伎俩。两人在一起谈艺论文,爱情也使张的创作热情高涨,写下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名篇。
这段感情很快就走向了尽头。张曾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还有那著名的“低到尘埃里”。她做不到胡兰成那种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洒脱,她想在乱世中寻求一份幸福安稳。然而张生性矜持高傲,胡兰成因此将张的不言不语故意理解为“慷慨”和“纵容”,一份婚帖困不住浪子,他很快就在武汉和周氏女子海誓山盟,然后又在日本战败后的逃离过程中和寡妇范秀美结婚。这过程他对张无一丝愧疚,反而恬不知耻地接受着张对他金银的接济。
张爱玲胜于她笔下白流苏等女人们的地方在于,她可以自食其力,然而感情上的挫败和笔下的人物并无二致,她曾说:“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这岂不是一语成谶?张在对胡死心后,其创作才华也如她自己所说:“只将是萎谢了。”后来出版的《华丽缘》,叙述多了黏着,令人感到“牵牵绊绊。”即使是乍暖还寒的《十八春》(后来修改更名为《半生缘》),也只是迎合读者口味,不断堆砌巧合事件的一部作品,可以说张在这部作品中已全然丢弃了她之前的观点——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同情的对象本身也充满着讽刺。她放弃了对意象的惨淡经营,也松懈了几分机智,《十八春》里恶人太恶,好人却太好。
后来新中国成立带来的一系列变迁,造成了过度夸张的政治氛围和难以名状的压力,这些令张难以接受。她独自一人逃往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在香港时写成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因为带有较强烈的反共色彩,至今也在大陆找不到踪迹。
在美国的日子里,张得到了在作家营地居住的机会,在这里她认识了美国的过气作家赖雅。这时张才三十五岁,赖雅已经六十五岁,由于在美国极度的孤独感,她就这样和唯一能聊上话的赖雅成为了夫妻,并且有了孩子(后来因为无法养育而流产)。然而两个人的境遇非常之困窘,赖雅年事已高,频发中风,婚后不久就变成了张实实在在的累赘,张本人这时又得不到什么工作机会,两人紧靠着一点救济金和版税前勉强度日。为了养家糊口,张熬夜写剧本做翻译,一度熬坏了眼睛。
回望张的两次婚姻,可以说有些不堪回首。带给张的,都是痛苦大于幸福,磨难多于快乐。一次是“人祸”,一次是“天灾”。他们都是由相识很快就走向了相许,对方和她也都是反性格的人,年龄又都大她许多,可以看出,张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正是她每次略显鲁莽走进婚姻的重大因素。余斌认为,张对胡兰成是真的怀有爱情的,对于赖雅,她是关上心门的,也许只是找个陪伴而已。但是张从未忘记过作为妻子的责任,无情也有义,陪赖雅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后来,心灰意懒的张就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
(五)绚烂终归平淡在美国最后的这三十年,张爱玲从写小说转变为了研究小说。这期间她潜心研究了萦绕她一生的《红楼梦》,其研究材料后来集结成了《红楼梦魇》。她还将吴语小说《海上花》翻译成了英文和白话文。又为其旧作做了一些增删,比如将《十八春》改为《半生缘》,又将《金锁记》增改成了《怨女》。然而这三十年的创作量加在一起,也不敌那一部《传奇》。后来她也有一些散文零散登出,也没有了她当年在上海完成的那部《流言》灵动,里面早已不见了生动的比喻和大量的隽语警句。议论都被节制了,剩下的都是平实。在广大的张迷心中,显然也是《传奇》、《流言》,而不是《红楼梦》考据和《海上花》注释,使张爱玲成为张爱玲。
年复一年,张爱玲一个人孤独地老去,几乎是隐身人海,鲜少有人能够见到她。即使这时她的作品已经在两岸三地再次声名鹊起,于她早已是身外之事。如此,“张爱玲之迷”笼上了一层凄凉,回望当年上海滩的大红大紫,想起她曾奇装炫人、名声显赫,再看她如今的境地,竟恍若隔世。
她是头脑很清醒离开人世的,年9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将重要的证件放进了手提袋,留在门边易被发现的位置,然后在睡梦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没有人知道她的离去。倒是日后,她的去世在整个华人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张之死成为了一个事件,张爱玲热也因她的去世而达到了顶点。
但是身在另一个世界的张爱玲已经无从知晓这一切了,她也并不关心。这些骚动,这些喧嚣,从来也与她不相干。她将谜一样的自己的一生留给了世人,由着他们去拆解、争论和玩味,而她,就这样悄悄地离席。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nanjizeiouz.com/krzz/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