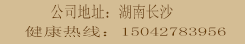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张爱玲闺蜜炎樱写给胡兰成的多字长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张爱玲闺蜜炎樱写给胡兰成的多字长

![]()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张爱玲闺蜜炎樱写给胡兰成的多字长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张爱玲闺蜜炎樱写给胡兰成的多字长
新书预告:胡兰成代表作《山河岁月》首次完整出版
一封信
——炎樱与胡兰成的谈艺录
文/炎樱译/张爱玲
兰你:
英文谚语“无知无识是幸福的”,真是有道理。我小时候听见广东人说一个颜色很“雅”,我常做是“哑”。因为这缘故,有一种新鲜透明的翡翠绿,他们说“雅”,我便大声抗议:“它不‘哑’,它会叫的!”我也不懂为什么大家茫然摸不着头脑的样子。直到最近我母亲才给我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了。但是太使人失望了,兰你,我想我的意思要好得多。不透明的,洋磁式的有许多色彩,浓厚的淀粉质的,什么都进不去,连回声都透不进的,那是完全石头似地又聋又哑。你只要看见一种洋磁式的杏仁绿的例子,就能意会到我说的那广大的沉默。(人家说“墙壁也有耳朵”,没想到他们的衣服也许不是这样的。)我希望能做一件暗哑的,无情的蓝衣服,我想也是很“雅”的。
兰你:为什么艺术家的长相都是瘦而饥饿的?去年夏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遇到一位作家。天气非常热,也许他走了很长的路,无论如何他是爬了许多楼梯。他是偏于瘦的,此外也很正常似的,西装穿得整洁漂亮。因为热,他把外衣脱了,哦兰你,你应当看见他的!这样的削肩,使人惊奇他的衣服怎样能够挂在身上的。假使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拎在空中,他整个的身体会从衬衫领口里掉出来了!
每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吧,走过狭小的地方,把身子一缩。除了物理上的,这也是心理上的关系,一定还是从前遗留下习惯,那时候我们遍体生毛,这样一缩,把毛都压平了,的确是有效。有一天有两个小孩在街上玩,大的一个比小的差不多要高一倍,他在一根铁杆底下走过,把头低了一低。小的一个走过铁杆底下──我看见了非常惊异──她也把头低了一低,铁杆在她头上总有一尺远。看着她真是可怕的,兰你,我简直不知道我要哭还是笑,我只愚蠢地吃吃笑了一声。真伤心呀,想着我们不过是一只羊,顺从法律与习俗,即使是与我们无关的—──好像我们自己现有的法律还不够多。
兰你,你真是不知道现在同爱玲一块出去有多讨厌。从前,虽然我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合理想的滑稽搭档,到底不十分引人注目,高兴在街上吃东西也可以。但是,怎样的呀!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那我还能够同情她们,因为我自己也最爱看人,但是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不那么莫名其妙地凑热闹,我有较好的事可做。前几天我们在路上正在笑着,因为我说了个笑话,忽然之间有人在我肘后叽喳喳,他手里拿着一件不知什么东西转来转去──后来知道是一本杂志一很心慌似地低声诉说。我正预备告诉他我身旁没有零钱,忽然听清楚了他是说:“呜,哟,哪,张小姐,喂呀,啊。”于是我明白了他是和爱玲打招呼。你知道有许多乞丐都是很上等的模样,而这位绅士新蒙上了一个与他不甚相配的旧光色,使他看去有一点绿,而且从我来看他不是中国人,所以他的中文稍微有点摇摇晃晃。幸亏我没有开口而出提到“零钱”的话。我真庆幸,后来我恨不得给一点钱给一个真的乞丐了。
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说我们喜欢某一个店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烧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够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吸着咖啡,一面冥想着糕与饼。
猪,猪,猪,还有猪!哪,现在我出了心头之气。路易斯错解了“风暴的蓝”,那并不是雨天下午几个人在一个咖啡馆里谈天说地。我现在倒真是“风暴的蓝”了。被一个名作家所欣赏,被用作题材,是很大的荣幸,我非常感谢的,可是我无论说了什么都被歪曲了,那又是一件事。难道我真的说了“个子高的人应当头发短”?当真我以为如此,爱玲的头发早就会剪短了,也不会留到现在!而且,要是你,你是否喜欢被形容作“圆脸,微黑,中等身材,会说话”?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下级动物(譬如说一只猫)对于一个人的虚拟的描写,或是一个植物学的学生在那里形容一只洋山芋,(一)它是固体,圆形;(二)外皮是棕色;(三)上面有细孔。结果一只洋山芋还是趣味毫无。我是完全同情洋山芋的,能够了解它的委屈。但是,兰你,我比可怜的洋山芋到底高一着,原来我“会说话”!它还会说话──多了不得呀。
我急于要告诉路易斯(士)先生──想想不说也行,免得言不达意,反而误会──我想告诉他我并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但是自从十岁起,空白的墙壁就诱惑着我,一直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有一堵墙可以尽情涂抹。然而,路易斯说我听到他说墙壁上好画图,我闻所未闻,高兴得快要拍手了。──他佩服我要见见我,又说了许多好话关于我,我再要这样地叽咕,实在我是个猪,但我并不是抱怨,不过是诧异得厉害。现在我通风换了空气了,“风暴的蓝”已经缓和下来变成杏仁的青了。──当然这不可以给别人看的,如法国人所说:“绝对的在四只眼睛之间”,你的和我的。
有一张留声机片你有没有听见过,渡边浜子唱的《支那之夜》?是女人的性质最好的表现,美丽的,诱惑性的,甚至于奸恶,却又慷慨到无理可喻。火星的居民如果愿意知道地球上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要把这张唱片奏给他们听,就是最流畅的解释。那歌声是这样的热烘烘的暖肚的,又是深刻,有利爪抓人的,像女人天生的灵机,同时又是很大量,自我牺牲到讨厌的程度。歌者也许并不是第一流的,可是这支歌她唱得不能再好了。
今天我看见一个女人,娇小的,但我想不是日本人,穿了沙漠绿的中国袄,(沙漠,因为是无尽的,又隐隐的带点沙黄)腰部勒紧了,下面大出来,广袖。年的上装,下面却穿了近于防空裤的,柔软地打了褶的深蓝裤子,一双明蓝绣花鞋。她臂膀里夹着个花布包袱,发髻低低地窝在颈项背后。她走路的摆动也有风韵,这边摇到那边,像一把扇子上的图画,只差看见画家的签名在左近哪里。
想起来了──你有没有告诉苏青我说她像崔承喜在那个中国节目里?崔承喜这里的姿态完全是苏青的闹哄哄的宁波风,圆而白净,可碰着,可摩的。和《观音菩萨》里的飘渺的崔承喜完全不同了。
新新公司附近有个游艺场的广告,画的许多跳舞女人之中,有一个非常使人想起苏青的叽哩喳啦的美。苏青见了要生气,因为画得很恶俗,单穿了件短短的淡红背心,腕际和脚踝上各围了一卷水钻闪光蓝荷叶边,短短的红白手腿,但是那浅红的鹅蛋脸,人情味极浓的笑眼,都是像极了她。不过需要细看,初看许多舞者都是一个脸呢?我常常特为多走两步绕到那边去,说:“去看看苏青好么?”爱玲一怔,我再加上一句:“──我们的苏青。”
你记得我说的我加入了圣约翰的一个学生会,最近我也领到一张表格需要填的。这么许多可笑的问句呀──你在家庭里是快乐的么?你喜欢醇酒妇人么?你有没有任何禁忌?你是真诚的么?你喜欢同男孩还是女孩交朋友?你偏爱的颜色是红、蓝、紫还是绿?最后,你应当慎重地思索,真诚谨慎的逐个回答。而所有的会员,二十几个男女学生,都把他们的回答美丽整洁地录写在一本大的簿子里。他们都很高兴吧,平常谁都没有问过他们这么些问句,谁也不对他们感到兴趣。……也许他们在家庭里的确是不怎么不快乐的吧?但我还是要笑!哦兰你,真的像我这样的是反常的吗?
哦,还有,现在的礼节到底是怎样的呢?说起来我是外国人不懂中国规矩。我们几个人弄了个小的跳舞会,请了一些同学。我诧异到极点,他们竟来问我:“为什么请XX和XX呢?”我差一点反问:“为什么请了他吗?那么,为什么请了你呢?”──好像有太多的中国青年以为潇洒就是无礼。
兰你,我第一样事情想到的,被介绍给路易斯(士)的时候,就是想替他剪头发。为什么一般画家、作家、音乐家,都要讲究一个不修边幅──常常也有坏的艺术家单只做到这一点。天哪,他们几时明白过来,用不着这样的化装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路易斯(士)时刻抱怨到贫穷,我这样地为他难过,差一点提议给他省了理发费──从前我在香港做临时看护,替我的病人剪过发的,你晓得。你想他听见我这样的不同凡俗的提议是不是会晕倒,虽然他是最名士派的?──而我实在是最最循规蹈矩的,世俗社会的栋梁!
爱玲和我在路上遇见我们从前的一个德国犹太女裁缝。爱玲说她每次被这犹太女人看见的时候如果恰巧不是穿得很清楚,就特别地觉得寒酸相。因为她笑嘻嘻地用这样的寻觅的眼光把人从头看到脚,还要伸手把衣服摸摸捏捏,什么都讲究一下。我也有同感。可是她同时也使人愤慨起来,使人要向她道歉说:“这件不好,我家里还有好的哩!”
和巴黎纽约隔绝以后,现在上海的装束可以说是穷极无聊了。难道不晓得什么都有一个适当的时间与场合。软缎显然不适于做运动衣,或是男式的裁剪,然而竟可以看见方肩膀,男式西装领的软缎上衣出现在耀眼明的正午的阳光里。又有一种严肃沉重的男性化的哗叽,做成一件浮体的女性化的外套,上面应有尽有,绣花之外再加上蝴蝶结。我并不是一味拘泥的人,但是这一类的东西看上去就是不对而且不好。尤其你应当看见老老少少的女人藉以自炫的一百另一双蝴蝶结。头发上扎了四只是不算一回事的。有一个中年太太头上戴了极粗的有色丝套,每一个太阳穴上缀一个透明的大蝴蝶结。蝴蝶结的本身当然并不坏。我甚至于想到把我稿费里的灰蓝与红的一千元钞票系两张在头发上。不是很俏皮的么,将得毕挺的样子。到铺子里吃东西,付账的时候可以叫侍者在我的头上现摘。说到这稿子,每次督促自己,总是强打着上海话和自己说:“作稿,作稿,糟糕,哎哟,糟糕来!”
哦,在我忘记之前,让我告诉你关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也和一般人一样地认为是个伟大的杰作,比《复活》好得多,更完全的。《复活》里的男主角非常使人失望,而卡媞亚,虽然面目朦陇,她是活的,确实在那里的。在《战争与和平》里,每一个女人,从娜塔霞,玛利亚,一直到宋雅,都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们可以觉得托尔斯泰是真心喜欢娜塔霞,但是他没有能够弄得她可爱,至少我是确切地不喜欢她的。也许这完全是主观的吧。娜塔霞做女子时候是这样的充满了生命,敏感的,差不多神经过敏,又是艺术化的,而她安顿下来做妻子做母亲的时候,却是那样地凡庸黯淡,自私的,精神上冻结了的。简直可怕。难不成她的精力与期望都是造作出来的,哄人的幻象?一旦找到了她在人生里的地位,马上她的吹得鼓鼓的才智就像个皂泡似地爆裂了。……我真心相信一个敏感的青年,如果是真的敏感到成熟之后绝对不至于变得这么无聊。无论如何娜塔霞是不能叫人满意的。至于玛利亚,她又整个的是个骗局。她同她那些“宗教上的朋友”我简直不能忍耐。也不怪她吧,大约托尔斯泰是要她自宽自解安心照抚贫民的,既然她得不到一个丈夫。她所有的宗教上的热诚都是从她父兄那里拣来的空壳。后来她到底现出了真身,在她的嫁后光阴里,为了一个宋雅鸡零狗碎地吃醋。
有一段我看了真生气哦,兰你,玛利亚的嫂嫂和法国女伴把她装扮起来预备相亲,越打扮越丑。这样地真实,可能的,我恨不得伸手进去干涉,她们的愚蠢急得我在旁边呻吟。其实生活里常有这一类的事发生,而且要继续发生的。
善良的宋雅是最可怜的一个,类如宋雅的人,不知怎么样的,即使是好人遇见了她,也把他们最坏的部分给引了出来了。罗斯托夫一家都是好人,在普通水准以上的,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要她牺牲,对她也没有真的谢意──这一点他们明明知道,甚至于讨论过。到底是他们不对呢,还是她本身的缺点?她是个荒瘠的人,可是你觉得罗斯托夫一家应当把幸福强迫到她身上的,如果他们真是好人,如果这女孩子真是不顾自己的,他们应当为她打算。然而,宋雅终于低三下四地生活在另一个妇人的家里,别人的孩子中间……
每个女人都写得软弱。男性的人物呢,合起来成为托尔斯泰的性格,从这里得到统一与完成。所有的男人都是可懂得的,活的,就连坏蛋阿那托尔,也使人同情,虽然也许不能宽容。安德雷是太好了也许,但他的好倒是真的。事实上他是这样地完美,无论哪一本小说里都没有一个女主角可以配得上他的。安德雷对于地球上的事实在没有多大兴趣,娜塔霞却有着强烈的污泥尘土的气味,他对于娜塔霞的爱决不会有怎样的结果的,所以他的爱半途而废了,也还是幸运的。不然一定不堪设想──所以他半路死了也还是得救。而且我们觉得像释伽牟厄,安德雷他也达到了他的涅盘,托尔斯泰在描写安德雷之中想必是四下里摸索着,归折他自己灵魂的一方面。
至于彼埃尔,开头他是最可爱的,后来弄了些宗教集团的胡话缠个不清,但是谢天谢地,这些到底给他摆脱了。
托尔斯泰在极短的记言记事里面能够有效地画出整个的个性,这种小品方式是不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就连个军官的一声不连贯的吠叫,也能够给他更多的生命,胜似多少页数的哲学分析。托尔斯泰真的不该谈哲学。他本能地知道应当说什么,做什么,但是理由他说不清楚──多半是并没有理由。罗斯托夫男爵,老将军,小配堤亚──尤其是他,像把太阳关在房间里,从门窗漏缝里都跑出光来,这样的活泼──还有那做衬衫的,就连亚历山大皇帝,都是这样清楚着实,可亲的。书里的男性所以有绝对的和谐,是因为他们实在是一个人的各方面──那人当然是托尔斯泰。
我不是极度崇拜俄国文学的人,但是有不少俄国人家为我所熟识,“复活”里我觉得活生生的是末了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囚犯的棚屋,俄国的污秽与俄国的汤发出浓浓的气味,囚犯们像上海有许多俄国人,再穷些也有本事弄得混身酒气油气。但是真的,俄国人还没有中国人一半有趣。上礼拜六我第一次去听苏州故事(译者注:弹唱),那里的空气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旁吃着金花菜,黄连头和芥菜,而又谈论个不休,说故事的人的风韵照样渗透了进来。其中有一对,父子二人,父亲费力地做了工作的大部分,儿子坐在那里纯粹是“摆看”的。他摆了个架式,自己不甚满意似的,又站了起来,把袍子拉拉好,小心地两脚交叉,轻轻把一只手放在胯骨上,另一只手悠扬地扇扇子。他是高大雪白的,据说有一些舞女每天晚上来听他三刻钟,还有次他的太太把他拉了回去。他们所说的故事里有一段,他父亲讲到一个杀人者,三个月没有被发现,享受着他犯罪的收获,但是最后,天理昭彰,官府要来捉了。他唱给他妻子听他夜里做的一个梦。真的兰你,爱伦坡也不能如此简单地制造出一种恐怖美丽的气氛──你可知道这故事是不是很老的?他梦见一道白光,一道红光,还有一圈牡丹花绕着他的颈项。妻子的角色由小白脸扮演,他鼓励丈夫说下去,用苏州的娇声应对着:“是个!难末哩?暧?”真是可记念的。
在我搁笔之前还有一桩事。有一家大的照相馆里陈列着一张照片,一个中国美人穿了西式礼服,衣服上下满是装饰,没绣花的地方全用珍珠盘了花。她坐在一张现代的沙发椅上,椅套上面织出模糊的花纹。背景的墙上挤满了光与影,她头上压满了珠花与卷发,她的鞋也是满帮花。唯一的空地是她的宽大的面庞,虽然长长的腮颊上没少塌胭脂,仍然是仅有的空隙,使人恨不得挂一点东西在她的空洞的表情上,一个朋友笑我没有知识,告诉我那是个著名的影星,我大大惊讶了,我们笑了又笑。真的我这人是缺乏信仰的。
但是“够了就是够了”。如同卓别麟所说,当他离掉了第四个妻子的时候──在他第五次结婚之前。
可怜的兰你,你今年在你那个地方要煮熟了。你有没有听见关于那美国人抱怨北京太热。旁边一个英国太太听见了便道:“这些美国人真是旅行家,哪里都去过!”
我写完这封信,拿起我社会学的笔记预备考试,你看我面前的东西:“每一个经验都是学问,学习就是经过一种经验,人生的经验是像科学里的学验。”现在你也替我难过吧?布嗬嗬嗬!
——选自《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唐文标主编,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年)
炎樱(年—年10月),阿拉伯裔锡兰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的同学,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知己。张爱玲的插画照片等都曾由炎樱创作着色和拍摄。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也是炎樱画的封面,且刊有几篇经张爱玲翻译的炎樱的文章。曾参与见证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礼。
新书推荐:胡兰成《今生今世》,槐风书社,年3月,布面精装,至今以来首次完整无删节版,比大陆简体版多12万字,而此前港台各版如远景版、三三版内容上也各有所缺。新版《今生今世》所剩无多,即将售罄,需要的请赶紧订购(扫一扫下图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taera.com/krzz/99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