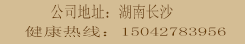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美景 > 经典重读张力壬管窥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美景 > 经典重读张力壬管窥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

![]()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美景 > 经典重读张力壬管窥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美景 > 经典重读张力壬管窥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
ZAL
管窥张爱玲小说中的
女性自省意识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级张力壬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有其独特之处,她喜欢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安插男女之间恋爱的小事情,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描绘普通生活的同时揭露人性本质抨击社会黑暗。她深刻成熟的女性自省意识让她直面现实生活中丑陋、病态、麻痹而不自知的女性群体,在克服性别错位、解构男性话语的同时努力拓展女性书写话语的空间,还原了被男权社会压迫摧残的悲惨女性。张爱玲对女性问题的深刻思考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新世纪的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和思想解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自省意识
SUMMER.TIME.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以及对女性作为独立的不依附于男性的人的价值的体验和认识,体现于文学创作上,就是女性自己拿起笔来以独特的话语模式,向千百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父权和夫权话语发起挑战的宣言。而在中国,女性意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而逐步觉醒的。代表新青年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掀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受到过现代教育的先进女作家,迎着新时代人人平等的曙光冲破千百年来男权社会下男尊女卑的黑暗,昂首登上了现代文坛。她们倡导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用文字塑造了一个个打破男权禁锢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抨击封建桎梏的同时歌颂了新时代女性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勇敢追求,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属于女性的一席之地,而张爱玲正是众多女作家中的佼佼者。
一、五四女性文学写作
以及张爱玲的独特性
(一)五四女性文学写作
五四之后女性文学刚开始萌芽,但是为了向社会传达出女性的声音众多新时代作家在创作女性文学的同时似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男权话语体系的影响,表现为通过模仿男性视角的叙事结构来构建女性的声音。这正是五四之后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女性文学作家在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女性意识之时所面临的被男性话语同化的叙事危机,几千年来的封建男权思想使他们很难从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找到解构和颠覆男性话语模式的有力武器,而不可避免的陷入利用性别错位和角色反串模仿男性话语来颠覆男性话语模式的怪圈。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家根据同时代女性的生存处境、社会背景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塑造了各种新时代女性人物。这些被压抑的女性形象以“变装”和“叛逆”的面目出现在女性作品中,构成极度反叛、个性解放的所谓的新女性,比如丁玲塑造的莎菲,蒋光慈塑造的菊芬,苏雪林塑造的醒秋等都是革命型女性的代表。但是这一模仿男性形象的革命女性的叙述模式,实际上成为了禁锢中国女性的传统封建男权的传声筒,是女性持续失去自我定位,在文学形象的塑造中再次被男性话语模式同化的表现。这种性别错位的文学现象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现实世界中几千年来的男权压抑和男尊女卑,使得女性群体长久承受着对女性自我定位的迷失和自身独立形象匮乏的焦虑,因此在新旧交替的转型阶段中,女性文学作家不可避免地借助模仿男性的革命女性模式来填充女性自身形象的匮乏,释放被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
(二)张爱玲的独特性
与同时期的其他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叙述模式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灵敏而熟练的,关于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她的思想和文字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关于女性独立存在的终极意义上。她反对那种“女扮男装”的革命女性形象,因为她认为这种形象塑造都掉入了模拟男性发声的怪圈之中而无法扮演真实的女性角色,且那种一切事情都奋力与男人并驾齐驱的“巾帼英雄”也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的待遇。这种看法和波伏娃的观点非常相似:“只要女人还在挣扎着去蜕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只要女性仍然不能正视男女之间的差异反而为此种差异感到自卑和低人一等,女性就还没有彻底冲出男权束缚的桎梏。
在张爱玲看来,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是因为其与男性之间有差异且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她在《谈女人》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男人回归男性本质,女人回归女性本质,只有这样男女两性才能建构起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因此,张爱玲在其女性文学作品中完全反对模拟男性的写作方式,不屑于塑造虚假的“理想化”的女性人物,而是抱着现实的态度,以古色古香却又处处透露着悲凉的文字揭露女性的真实面貌和尴尬处境,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那一时代真实的女性人物的复刻,即使再麻木压抑,病态疯狂,张爱玲都没有选择刻意回避和美化。这种写作方式跳出了性别换位的怪圈和制约,同时最真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带有一定的对女性自身的审视意味。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
女性自省意识
张爱玲的作品从审视女性自身缺陷的角度出发分析女性的千古悲剧,认为女性内心深处以男权为中心的奴性意识、畏惧男性的孱弱心理和懦弱性格,是女性解放自身的重要障碍,张爱玲曾经直言“女人的确小性儿,矫情,作伪,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而造成这种女性心理的根本原因,正是千百年来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的压迫。张爱玲通过描写各种压抑,病态乃至疯狂的女性形象,看似是对女性的内在缺陷的自省,实则更深层次的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本文主要总结了张爱玲作品中三类常见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迷失自我的女性
所谓迷失“自我”,是指女性在被生存、欲望、婚恋、世俗观念等物化,或被男权(父权、夫权)奴化时,所体现的主体丧失与模糊,从而沦为他人的附属品。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新时代女性们也会经常不惜放弃自己的追求,呈现出懦弱,退缩和奉承的传统女性姿态。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受到过一定的现代教育,敢于和风流成性、脾气暴躁的丈夫离婚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人格。但出生于封建大族书香门第的她在骨子里却仍然秉持不可动摇的封建思想,她将婚姻视为自身生存的保障,选择再嫁的最初动因也是为了维持生计,她本可以在与前夫离异之后选择自力更生,走向她最开始所追求的独立自主、男女平等,但她并未这样做。逃离残暴丈夫的白流苏却并未逃脱封建男权的禁锢和迫害,她的哥嫂在挥霍完她离婚后的钱财之后不留情面地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受够了娘家人的冷嘲热讽,白流苏将自己的命运作为赌注,孤注一掷地来到香港寻找范柳原。至少在刚开始白流苏是不爱范柳原的,她只是想利用他的钱财获得一张长期粮票,但假戏真做后香港城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使她成为了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白流苏具有一定的新时代女性的特质,面对丈夫的残暴和风流成性,她敢于反抗,离婚后也敢于再次追求自己的幸福并最终赢得了爱情;但从维持其自身女性主体性的角度来看,她又输得一败涂地,她之前所有反抗男性权威的努力不过是让自己摆脱了一个男性的奴役而成为了另一个男性的附庸。在追求所谓的独立的过程中,白流苏逐渐迷失了自我。
再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也是一个想要追求独立,却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的典型。葛薇龙本是一个单纯独立的少女,因父母返沪而孤身一人留在香港寻求混迹于香港交际圈的姑妈梁太太的帮助以求继续完成学业。初到姑妈家时看见衣橱里一大堆漂亮华丽的衣服,还非常不安地谴责自己:“一个女学生那里用得着这么多?这跟大三堂子里头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在决定寄居于姑妈家后,葛薇龙还经常安慰自己:“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当她意识到梁太太只是想要利用自己笼络男人以满足她的情欲物欲时,她有过想离开香港找份平凡的工作有尊严的养活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却发现自己已经对奢侈糜烂、灯红酒绿的生活产生了依赖,她已经心甘情愿的被金钱和虚荣困住了前进的脚步。当葛薇龙发现乔琪乔不过是个花花公子时,生气的她最后仍为了有体面的生活最终选择了忍耐并与他结婚。葛薇龙一开始曾经告诫自己不要像姑妈梁太太一样极力讨好男人,可是到最后自己却成为了一个依靠男人、为男人而活的女人,一个自愿奉承男人的“风尘女子”。
(二)丧失母性的女性
张爱玲认为女性的本质是一种具有神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等特点的女性原则,“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母性,是指身为母亲的女性所具备的“关爱儿女”之特质,即母亲的自然属性。母性总是和女性特质关联在一起的,然而当时自然博大的母性在长期以来的男权统治下基本已经完全异化或消失殆尽,呈现出丧失慈爱、不顾儿女幸福、残忍暴力等病态处境。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这类女性中的典型,七巧在少女时因哥哥贪图金钱而不情愿地嫁给了一个性无能的丈夫,在爱与性上都无法得到满足,且在刚嫁入姜公馆时,她总是处于被欺负被轻视的地位,和姜季泽之间的暧昧情愫以及感情纠葛更是加剧了她内心的压抑和仇恨,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七巧在母性以及人性上的异化,甚至是兽化。七巧继承财产自己养育儿女之后,在家庭中反过来扮演着“施虐者”的角色。“长白悲剧”是一部母恋情结的人伦悲剧,是七巧在得不到自己的爱情后情感转移所导致的病态行为。她先是千方百计地给儿子长白娶妻,但却在娶妻后马上盘根问底地询问长白的房事,并在公共场合取笑她们,使儿子、儿媳颜面尽失,先后逼死了芝寿和绢姑娘两个儿媳,七巧为了将儿子长白牢牢拴在自己的身边,不惜教儿子吸大烟,七巧的种种行为使得《金锁记》从头至尾充满着一种压抑病态的氛围。更为可怕的是,七巧通过破坏女儿长安的婚姻和幸福,最终造就了一个“小七巧”。“长安悲剧”是一种母女敌视的性别悲剧,是女性之间同性相斥的本能反应。七巧自己在少女时期是没有体会过真正的性与爱的,因此当她看到女儿长安和表兄之间无意的身体接触,抑或长安和童世舫之间的感情时,作为母亲的七巧却显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嫉妒,她不仅要压制长安的以及他人对长安的情感欲望,在新时代仍然逼迫长安裹小脚,教她抽大烟,更是在长安即将结婚时设计败坏了女儿的名声,彻底毁灭了长安未来一生的幸福。男权社会的压迫、少女时期的经历以及对金钱的疯狂追逐,使得七巧与生俱来的母性被吞噬了,甚至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并最终用套在自己身上的又爱又恨的黄金枷锁亲手砸碎并丧送了儿女的幸福。
此外,张爱玲作品中丧失母性的女性形象还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利用自己的侄女葛薇龙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和物欲的梁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因为自身的婚姻不幸而对自己的女儿们缺乏必要的性教育最终剥夺了女儿女婿们的幸福的蜜秋儿太太;以及《花凋》中因为害怕给女儿治病而暴露私房钱,便狠心看着女儿死去的郑夫人等,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一味地害怕、顺从、奉承男性而导致了自己母性光辉的泯灭,最终造成了两代人的悲剧。
(三)压抑病态的女性
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女性,无论她们是否接受过现代教育,却依然将男权社会下的封建桎梏以及“三纲五常”等奉为圭臬,不会甚至不敢做出任何反抗,最终酿成了一生的悲剧。她们中的很多想法和行为在现代人看来甚至压抑奴化到一种病态的倾向。
《连环套》中的主人公霓喜,一辈子都渴望拥有一场正常的婚姻经历,但是她在追求婚姻幸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卑微、虚荣和不自爱,完全展露了她内心病态的奴化倾向。霓喜生长在广东乡下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少女时期被养母卖掉,对贫穷的恐惧让她自始至终都在寻找一个有钱的男人作为依靠。她先后至少与三个男人姘居却都没有取得过合法的妻子身份,三个男人来自印度、中国、英国三个不同的国家但是都不愿意把霓喜当做自己的合法妻子。霓喜面对一个又一个男人,不断的跳入渴望婚姻的欲望的陷阱,却一次次的希望落空。到最后已经日渐麻痹的霓喜不得不通过假爱奉承来追求物欲获得快乐与满足,利用自己尚存的几分姿色来满足自己,即使不是合法妻子,她也喜欢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贵生活。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设置的情节正如小说名称一样一环套一环循环往复,衬托出主人公霓喜在无法实现的婚姻生活中的奋力挣扎。霓喜所经历的每一次男人的骗局,都是因为她内心对于婚姻,对于金钱的强烈渴望而造成的,因为渴望,她拼命地抓住每一次可能成为男人的妻子的机会。即使希望渺茫,即使她追求婚姻的方法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压抑、悲伤和痛苦,霓喜始终像上瘾一样地以一种“被迫自愿”的态度混迹于每一段感情之中,正是因为男权社会下婚姻才是女性唯一出路的观念让惧怕农村贫穷生活的霓喜无法逃脱“连环套”的悲惨命运。霓喜在传统的吃人的思维模式下自甘堕落,投入一段段她认为的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最后堕入情欲物欲的深谷,以填补她追求美满婚姻的道路上所留下的遗憾和空白。霓喜是被传统婚姻观念所奴化了的女性,她一生都在寻找可以真正把她当做妻子的男性,这种寻找已经成为霓喜生命中近乎病态的本能,她的悲哀自然无法避免。
除霓喜外,《茉莉香片》中因顾虑封建伦理道德自愿将自己“绣在屏风上”的冯碧落,《心经》里具有病态的恋父情结的许小寒,《琉璃瓦》中屈服于父权包办婚姻的长女静静等女性,都是受到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的戕害而甘愿受委屈也不愿为自己的未来去抗争。张爱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或明显或隐藏地将女性的种种病态行为放置在男权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在对女性自身缺陷进行自省的同时批判父系文化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囚禁。
三、自省后的思考
张爱玲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描述那一时代女性的真实困境,审视阻碍女性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聚焦于那些多少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却又依然挣扎在旧家庭旧社会的女性。五四之后千百年来深受压迫的中国女性开始追求自由独立和男女平等,但是封建伦理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无论是一出生就被困于深宅大院或生长于穷乡僻壤的传统女性,还是上过女子高校、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无一例外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封建女性麻痹而不自知,毫无怨言地站在男人背后、被男人支使;而所谓的新女性却一边宣称自己要追求独立和平等,一边却固守以男权为自身生命支柱的传统意识。正如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说的:“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张爱玲通过女性自省意识揭示了女性内在的缺陷,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让新时代的女性们有了一定的个性和想法,但是自身仍然无法摆脱骨子里的奴性而使得她们的奋力挣扎更显悲凉。张爱玲通过女性自省意识巧妙地抓住了这样的反差,揭露了每个女性的抗争在时代大背景下的无力和无奈,让这些人物的命运更显真实和悲惨。
和其他同时期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女性书写的特别之处在于大量书写女性自我的迷失、病态、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这一带有女性自省意识的文学创作手法,巧妙的将反思女性自身缺陷和反对封建男权压迫的两个主题结合,在讲述女性群体在封建父权文化压迫下压抑病态的现实处境的同时,更通过这种病态现实和真相试图去抨击和颠覆男权话语和封建父权文化,达到一种“事实胜于雄辩”的抨击效果。
四、结论
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女性由于长期的文化生活习惯和千百年来的封建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内在阻力。这正是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所要呈现出的问题,她从女性本体生活切入,通过对各类女性生存遭遇的描绘和心理状态的剖析,揭示了广大中国女性群体深层意识中的传统印记:尽管女性在外貌服饰以及生活方式上有所改变,但是女性的生存本质和内在思想并未发生根本上的变化。不少新女性通过读书和工作走向社会,向男女平等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骨子里却依然是男性的附庸。这种附庸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微和奴性,但是根本原因仍然是封建伦理道德和父权文化的压迫。正是意识到了这种问题,张爱玲才从人性的角度,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审视。上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揭开了蒙在女性身上的各种面纱,这种清醒成熟的自省意识是张爱玲的女性意识的基础,也奠定了张爱玲女性文学创作的人性深度和高度。
参考文献
[1]李掖平:《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2]林幸谦:《张爱玲和五四女性文学的逆向写作》,《职大学报》,年第5期。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年版,中译本。
[4]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
[5]沈丽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病态现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
[6]谢理开:《论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流变》,《绥化学院学报》,年第2期。
[7]张爱玲:《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
[8]黎莹婧:《荆棘林里的红白玫瑰——管窥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畸变》,《名作欣赏》,年第12期。
[9]张丽媛:《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安徽文学(下半月)》,年第3期。
[10]宋剑华:《“金锁”未必是“金钱”——论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自省意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11]闫秋霞:《论张爱玲对“家”的拆解》,郑州大学年硕士学位论文。
[12]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
文章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代表“薪火CUPL”立场,由于排版篇幅所限,注释从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
张力壬
图
来源于网络
本期责编
罗小媛
审核
张格乐
我们有满腹的诗书
我们有高远的志向
我们有坚定的眼神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珍贵的缘分
SUMMER.TIME.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taera.com/krmj/99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