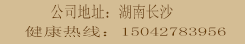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文化 > 张爱玲逝世21周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对照记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文化 > 张爱玲逝世21周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对照记

![]()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文化 > 张爱玲逝世21周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对照记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文化 > 张爱玲逝世21周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对照记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对照记
文:河小西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张爱玲《小团圆》的开头,雨下在九莉的天空,也下在张爱玲的心头。虽然张爱玲口口声声说自己写《小团圆》是为了讲一个“热情故事”,可是从故事叙述的笔调来看,依旧是张爱玲最拿手的“万转千回后的幻灭”。
今天,是张爱玲逝世21周年的日子,让我们重新走进这个孤独的人的内心世界。
“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
年9月8日。“叮玲玲……”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吓了一跳,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电话是张爱玲伊朗房东的女儿打来的。她对林式同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林式同匆忙赶至张爱玲位于西木区罗切斯特街的张爱玲公寓,见到了张爱玲的遗体,还有她临终前简短的遗嘱。
张爱玲最后的遗嘱用英文清清楚楚地写着两条,翻译成中文是:
1、我死后,我的所有遗物都遗赠给宋淇、邝文美夫妇。
2、我希望立即火葬――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如果撒在陆地上的话就撒在空旷处。
“张爱玲遗嘱没有提《小团圆》一事,白纸黑字,一切‘遗嘱要求销毁’言论是谎言和妄言。”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先生急于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
这份最终遗嘱中确实没有提到《小团圆》的名字。关于张爱玲要求销毁《小团圆》手稿的要求出现在她更早的遗嘱中。年,张爱玲把当时的遗嘱正本寄给宋氏夫妇,其中说到了要将《小团圆》销毁,但是宋以朗强调,在同时寄来的一封附信中,张爱玲的态度又显得模棱两可,她说:“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
张爱玲显然对《小团圆》珍视有加。夏志清说她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但直到她在26年之后去世时,也没有见到这本书变成铅字。宋以朗先生珍藏着年张爱玲给宋淇(Stephen)的去信,在此信中,张爱玲希望宋淇能为他帮忙在港台地区连载《小团圆》并出书,其心情是如此迫切:
Stephen,
“小团圆”因为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倒已经写完了。当然要多搁些天,预备改,不然又遗患无穷。平鑫涛那三千美元是预付连载稿费,作二十万字算。我告诉他,绝对没有二十万字,连十万字都还是个疑问。好在就快了,还是到时候再算字数。我因为没功夫去邮局,支票撕了寄还,没挂号。前后写了三张便条解释,想必他不会误会。这篇小说有些地方会使你和Mae替我窘笑,但还是预备寄来给你看看有没有机会港台同时连载。如果没有,就请空邮寄给平鑫涛,皇冠早点连载完了,可以早点出书,乘台湾还在,赚两文版税。上次“二谈红楼梦”,我当然赞成平邮寄去,而且要与香港刊登得合拍。上次寄来的二十元邮报费似乎没兑现,也许不在手边。再寄了一张来,省得费事找。平鑫涛又建议“谈看书”等出本散文,我告诉他都包括在文化生活预备出的集子里,如果搁浅了,他要是有兴趣就跟你商议,我都托了你全权代理。“谈看书”后记登在中国时报上很好。我不跟他们讲价钱,根本不通信,登了也还没寄来。我想我对红楼梦的看法跟你有点不同,因为我自己写小说,所以注重对白,认为这种地方是书的神髓。Hawkes的英文当然好到极点。――要到邮差来之前下楼去寄信。Mae和你都好?
Eileen
九月十八日
宋以朗:我这样继承张爱玲的遗产
当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拿到张爱玲从美国寄来的手稿时,他既感到兴奋,又觉得踌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小说中的指涉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担心当时尚健在的胡兰成会以这本书作为一个契机出风头和占便宜。当然了,其中与政治有关的用语又将此书在台湾的出版变得前景难料。“被禁”?也是很可能的事。宋淇的心头直打鼓――都是因为张爱玲所谓的“无赖人”胡兰成。
宋淇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所以他委婉地劝告张爱玲暂时将这部书收藏起来,待时机成熟再出版不迟;但是对于张爱玲见出版无望,赌气式的说要将小说手稿付之一炬时,宋淇夫妇也并没有太当回事,只是将其束之高阁而已。
在《小团圆》繁体字版前,宋以朗为《小团圆》写了长达字的长篇序文,为自己没有销毁《小团圆》辩解。他说,即使退一步,这是“违背了张爱玲的意愿”,那么“家父早在至年间就已堂而皇之的违背了”。
“假设你收到‘《小团圆》要销毁……’的信,你会怎么办?”宋以朗反问,“借你一个胆,你也不会把它烧了吧?朱天文对我说,希望我能促成这本书的最后出版,但是我的决定没有受到任何个人的影响。正如我在《小团圆》前言中所说的,我一个人整理和考虑了张爱玲的第一手文献,并非如媒体所报道的,我听从了他人的意见。”
年,张爱玲把遗嘱正本寄给宋氏夫妇,要销毁的做法恐怕也是因为出版无望的绝望,而在附随的信上说:“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张爱玲的犹豫也尽显无遗。
《小团圆》是张爱玲晚年的心血之作。宋以朗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地保护它,他真地狠不下心肠把它销毁。因为摆在宋以朗面前的手稿复印本,是整整页缮写得非常工整漂亮的定本,“绝不是修修改改的草稿”,宋以朗强调,宋以朗说他当时的心情是“简直震撼得呆了”。
宋淇、邝文美结婚照
这让他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和张爱玲的第一次见面:“年夏天,张爱玲为了给自己的美国丈夫赖雅筹集医药费,回香港赶写了两个剧本--《南北和》和《南北一家亲》(这两个剧本的第一稿都是家父写的)。那次她先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后来,也就是年的3月,她直接住进了我家中。”张爱玲终日足不出房,只顾埋头写作,但是,也许是时间久远的缘故,宋以朗对我说他并不太记得当时的情况:“我只记得她很瘦,人挺高,说一口上海话,除此之外,其它都不记得了。”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母亲邝文美是张爱玲的挚友。年以后,宋淇来到香港,遇到银行倒闭,家财尽失。此时没有办法,宋以朗说父亲愿意做任何工作,后来美国情报部门给了他一份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他们的翻译工作,“这也是家父之所长”。
在香港,宋以朗的母亲经常在九龙、港岛与张爱玲一起喝咖啡闲聊。张爱玲之前出版了一本《张爱玲语录》,收录了张爱玲的只言片语,但多有漏网之鱼,宋以朗说,他一直在编辑这本语录:“我保证这本书和原来的那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宋淇夫妇全家福
除了语录,宋以朗也一直在整理张爱玲和他父母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有40万字之巨,要将他们全部整理完,对于宋以朗来说的确是一份吃力的工作。不过他也觉得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而已。
宋淇夫妇去世之后,宋以朗先生顺理成章地成为张爱玲所有遗物的法定继承人。因为版权,他可以得到合法的版税,这些钱他用来整理出版那些还没有出版的张爱玲著作和书信,宋以朗从未以张爱玲的名义创立基金会,但是他以张爱玲的名义在香港大学创立了一个万港币的纪念奖学金。“我想,她不会喜欢一个非常正式的机构。她宁愿是低调的,”宋以朗对我解释说。“我相信不论是张爱玲还是我的父母,都不希望这笔钱用于我们自己,因此,我将这些钱都用于与张爱玲有关的事务。”
张爱玲留下了14箱的遗物,除了书稿和信件之外,还有眼镜、化妆品、梳子、手表、毛毡等等,大部份存放在台湾皇冠出版社。
其中有些原本就是宋淇送给张爱玲的,比如宋淇的一部牙牌签。张爱玲很喜欢它,大凡“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但是宋以朗并不认为张爱玲是个很迷信的人:“当你坐着等待一本书的消息时,你可能会期待着某些预兆,因为除了等待之外,你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读了《小团圆》开头和结尾时关于等待的描写,你可能会对张爱玲着迷于牙牌签的心情有所体悟。”
宋以朗先生
苍凉的悲剧
对于张爱玲本人,宋以朗印象模糊,但是对于她的小说文本,宋以朗读了一遍又一遍。我问他,宋淇曾建议将男主人公角色改为双面间谍,并被人暗杀,但被张爱玲拒绝,是否觉得张爱玲是个固执的人?宋以朗说不会啊,“反而是我觉得,她有坚持,没有让现实生活中的叛国者变成一个双重间谍。如果真地就此认为张爱玲很固执,那反而是个很愚蠢的念头。”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将自己与那位“无赖人”的爱恨情仇描写得令人不寒而栗。面对这位汉奸、朝秦暮楚的浪荡子、张爱玲悲剧人生的一手制造者,张爱玲也曾经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但是他的薄情、他的寡意,他迹近游戏的感情纠葛,终究还是压倒了他韶华胜极的文笔功夫留下的美好印记。
张爱玲终究忍耐不住,要“自己来揭发”。如果我们相信这本书就是张爱玲的自传的话,那么我就能从书中了解到一个男人的无情和一个女人的多情将会蜕变成怎样苍凉的悲剧?除了胡兰成,还有更多的男人,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也是悲剧。九莉在公共汽车被人欺负,后来成了著名戏剧家和文化领导人的荀桦“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为了和赖雅的那段清苦的生活,张爱玲堕过胎,眼睁睁地看着四个月的胎儿被抽水马桶冲走……
心痛,也许是痛到心底的。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又是一个“罗生门”,将胡兰成的书写和张爱玲的描述对照起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在胡兰成版的《今生今世》中,胡和张的爱情纯洁到了极点,胡兰成一见张爱玲而喜,再度则惊艳,继而执子之手,两情相悦,活脱脱两个赤诚的男女,抛妻之事似乎也多了几分徐志摩式的情有可原,于是,有了后来严浩《滚滚红尘》中乱世儿女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可是张爱玲的《小团圆》则将这种美丽统统戳破,正如她在《小团圆》的结尾时所说的:“这样的梦只做过一次,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
尽管之前张爱玲也喜欢从房门外偷偷地端详胡兰成,也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安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但是从性格上就决定了,张爱玲总是从秽亵平俗之处看到人生的美、人生的悲凉,“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胡兰成语),是《红楼梦》中人物;而胡兰成仿佛是她的一面镜子,沉溺于情感的游戏,也许可算是《金瓶梅》中人物,又是她真正的解人。这样一对冤家碰到一起,擦出多少爱情的火花和仇恨的怒火,也只有当事人了解其中的真相,旁人大概是无法简单地说谁对谁错的吧?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这本从尘封中翻出来的长篇小说,人们将太多的目光集中在爱情双方的八卦上了。除了《小团圆》,张爱玲之前两部早就在海外出版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却一直无缘内地读者,其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暴露无遗。比如顾彬就完全否认其中的反共倾向:“我很早就读过这部小说的英文版,五十年代就读过了。她对中国大陆的现状有距离感,但是她很客观地描写了当时的历史。当时她拿了CIA的钱,但《秧歌》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文学作品。”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不是本身也是一种苍凉的悲剧?
张爱玲在美国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在一起
生命像一袭袍子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印象中的张爱玲与时尚无缘。说到夏志清与张爱玲的相识还要追溯到年,当时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的一位毕业生章珍英女士召集同学在自己家里办派对。夏志清也应邀出席。那天碰巧张爱玲也跑来凑热闹,夏志清印象中的张爱玲和照片中的不太一样:“那时她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张爱玲的眼神不太好,在40年代就已经近视八九百度,所以只好戴个“啤酒瓶底”,不然估计寸步难行。也许就是个煞风景的眼镜片掩饰了张爱玲全部的美,她自己和同学们聊天时也显得不够大方,比较腼腆,有些缺乏自信的样子,夏志清并没有太在意她(当时他也没有怎么读过张爱玲的小说)。这次聚会夏张二人相识却不相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夏志清完全为一个名叫刘金川的娇小女子给迷住了。这位宁波小姐绝对是那天派对上的明星,夏志清说她的笑容、脸型、容貌都有些《莎翁情史》中女主角葛妮丝·派特洛的意思,脾气又好,心肠又软,身材玲珑又偏是夏志清钟意的那一类型,怎不把他迷得神魂颠倒(到了晚上躺在自家的床上还在想她)?哪里还有闲心注意到张爱玲呢?直到50年代夏志清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才忽然发觉人不可貌相这条“面相学”上的金刻玉律果然有些道理。
年轻时的夏志清(右)和哥哥夏济安
而在王惠玲的《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中,张爱玲却俨然一位时尚教母。在裁缝边上指手画脚的张爱玲有这样一句台词:“再长一点!不!短……短一点……这边……”虽然不过是日常的对话,用来描述张爱玲的恋衣情结倒也恰到好处。张爱玲对服装的精益求精与她精巧的文字之间多少有些重叠,仿佛她在构筑一座文字之塔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织一件衣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生命像一袭袍子”。
每一个妙龄的女郎都会对服装特别敏感,这本是常识,但在张爱玲,这种敏感和占有欲望似乎太过招摇,而成了张爱玲小说及其身份的徽章。漫画家文亭曾经为当时上海滩的三位“文学宝贝”作过一个有趣的“女作家三画像”。辑务繁忙的苏青、舞蛇者潘柳黛和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三足鼎立,可见张爱玲的“摩登着装”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之深。有相当一段时间,张爱玲的穿衣打扮和她的小说创作并驾齐驱,俨然成了文学性想像之外的另一种风情。她的时装:裘衣、锦缎、“大镶大滚”的皮袄、DIY的碎花旗袍,在让观者顿生艳异之感的同时,也让张爱玲本人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也许是小说给她诉说穿衣哲学的空间还不太大,她甚至还给《二十世纪》杂志写的一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的专论,其中所有女性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由张爱玲本人一手包办。罗玛说张爱玲的着装有着强烈的怀旧意味,证据就是许多都由族亲的旧衣改成,却没有看到,那些原材料几乎都经过了张爱玲本人的巧手编排,它们的趣味格调与所谓的怀旧迥然不同,全都染上了现代社会的胭脂。
这位没落的贵族通过小说和服装在她的身体上复活了名门望族的骄傲,激起了她强烈的成名渴望。她要人们向她喝彩,向她顶礼膜拜,就像她的家族曾经拥有的荣耀一样,说穿了,她的目标不外乎就是要达到胡兰成所说的“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而服装正是最直接、最具有视觉魅惑力的一种手段;此外,时装还是地位的象征,是将她与穷人们划清界限的一道屏障,即使在最张爱玲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这种青年时的嗜好--年时的张爱玲不论是年龄还是经济状况都无法与40年代相提并论,不过张爱玲出席宴会时的一身打扮,仍让在座的先生小姐们啧啧称奇。
通过服装,她自恋、自我标榜,在文字上塑造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带上了张爱玲尚未磨灭的贵族气息。王安忆说她世俗,只不过说对了张爱玲的一面,那些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到了张爱玲典雅、精致的文字中就仿佛具有了另一层面上的意义。相对于苏青的物质趣味,张爱玲用心描摩的却是人世的荒凉,感受最深的也是无边无际的幻灭之感。早年家境的困窘对张爱玲的来说不啻于一场噩梦,这场噩梦笼罩在她的心上,让她自卑和自闭,也让她幻想着苍凉的人生之外的无端的快乐,虽然结局往往仍以虚无和清冷而告终。
我想,要真正地了解张爱玲,最根本地就在于去领悟一种困扰着她的两难处境:张爱玲的骨子里隐含着她对这个时代的仇恨,对家庭深深的惶惑和不信任都在折磨着她,却又像一个陷阱一样让她沉溺于此,无力自拔,恰似这件她要做的衣裳,是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
高处不胜寒
张爱玲是小资的,但正如夏志清所看到的,这种小资恐怕还不能代表人们对于旧上海远东第一大都市流光溢彩的印象。严格说来,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恐怕更符合后来人对十里洋场女性的想像。尽管是亚洲人,却长着“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那高耸起来的胸脯,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充满了难以抵挡的“异域”诱惑力,她是肉感的、情欲化的,以当时电影中的艳星(比如嘉宝、克劳敷或谈瑛)为理想的模型。没有人知道刘呐鸥和他的朋友们是不是真的艳遇不断,但至少他们的小说沉醉在“东方的尤物”的包围圈中,而张爱玲却全不如此。《心经》中的许小寒也很漂亮,甚至被张爱玲称之为“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然而,她的脸却只是“神话中小孩的脸”(当我们在聆听苏芮的《亲爱的小孩》时,想必绝不会哪位多事者把这位小孩与莎朗·斯通或者麦当娜那样的性感女神搅和在一起),小孩消解了强加在上海女性身上的那种想当然的妖魔化倾向,赋予了她一点纯真。也许正因于此,《心经》中的许心寒要比“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一片”的上海要来得高一些,在小说中出场的时候,她“高高”坐在白宫公寓屋顶花园的水泥栏杆上,介于天和上海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位置也可以看作是张爱玲自我定位的结果。
这个自诩为“天才”的张爱玲自视甚高,她确实喜欢都市中的汽车鸣笛、摊贩叫卖、电梯轰鸣,炉膛里冒出的青烟,各种时尚杂志和以八卦新闻为主业的小报,但更多地如王安忆《长恨歌》开场时的景物描写一样,多少带有一点俯瞰的姿势在看上海,仿佛许小寒一样,坐在“不胜寒”的高处,冷眼旁观着这座都市的生生死死,这样眼光下的小说怎么能不多一些悲怆,少一些红鬃烈马一往无前似的热烈和乐观?她的小说的色调几乎清一色都是清冷,在表面上热烈推崇城市之余,也流露出张爱玲内心深处对于都市的矛盾情绪。
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她和那位游走在巴黎大街小巷中,被现代这只怪兽所震惊的波德莱尔一样孤独,只是波德莱尔选择在都市人流中行走,而张爱玲则选择遁世,从一个如公寓的窗口般的地方望出去,然后可以将那些曼桢、曼璐、曹七巧、杨太太之流的人物娓娓道来。她的态度并没有浪荡子刘呐鸥般的轻浮,恰恰相反,诚如夏志清所说:“她的态度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新兴都市的建立必然导致古典社区和人伦规范的解体,张爱玲的出身使她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红楼梦》中家族的凋零、贵族高雅文化的没落的时代大悲剧。张爱玲的小说,就像是在一座老房子里置放了些新家具,意识是新的,而文字、意境却统统有着一种古典之美,而这古典的美就在喧闹的都市中沉淀下去,成了一座“冷宫”,这些生活在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男男女女,就像是韶华飞逝的宫女和帝妾,虽然外人看着是繁华热闹,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空荡、烦恼、也许还充满了死气。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一文开宗明义:“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食月下的青灰色。”
张爱玲绘画
左派的忧郁
在张爱玲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左派的忧郁”,这和她的公寓生活大有瓜葛。她喜欢公寓,但问题在于,她对公寓的热爱并不源于公寓这种现代主义风格的连排式住宅的时髦与新鲜感,而在于它的“冷”。有很多研究学者都从《公寓生活记趣》中读出张爱玲的都市情结,却完全忽略了张爱玲开门见山的几句话,不晓得算不算是有意的误读。她这样写道:“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要说和当下上海那些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比较起来,6楼实在算不得怎么稀罕,温度也不见得真能降下几度,但在张爱玲,这“空中楼阁”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一个世俗场所,更是她最合理想的“逃世”的世外桃源,一个“大隐隐于市”般的“都市里的乡村”。公寓的冷契合着她对这个世界(包括上海)的悲观想像。她说如果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从底下生出来;她写梅雨时节地基陷落、门前积水,屋子里闹水灾时的情景--那些糊墙的花纸上斑斑点点的水痕和霉点,仿佛长在她的心坎上一样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虽然一贯的平静,却也难掩饰内心的凄凉,这何尝不是张爱玲人生与写作的一个缩影?
爱丁顿公寓(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和她的姑姑住得时间最久的公寓(年住在51室,年以后在65室)。这里有两个单元,张爱玲和姑姑有各自的卧室和盥洗室,中间是厨房和阳台,阳台是意大利风格的,就是在这里,她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遥望远处高楼玻璃窗上的一块胭脂红,才蓦然发觉那是元宵节的月亮。晚烟里,她俯瞰着显赫的上海,“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右前方是大名鼎鼎的哈同花园,现在只剩下了一些余绪,越来越稀薄。
童年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还有,和胡兰成的秘密结婚以及离婚。就是在这幢普普通通的公寓里,有兴致时,胡兰成也随了张爱玲去静安寺的市街上去买一些小菜,张爱玲则喜欢从房门外偷偷地端详胡兰成,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安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但对于胡兰成这位情不能已的情场浪子来说,这段爱情注定只能成为张爱玲的悲剧。胡兰成自己说,他平生喜欢两样东西,一是女人,一是坏人。他投敌叛国,在民族气节的大事上,坏得可以,对于张爱玲,他同样不能算是一个好人。有一次,在路上,张爱玲居然与胡兰成的一位情人,这位情人出于一种怎样的傲慢竟当场羞辱了张爱玲,张爱玲虽恨胡兰成的滥情,却也无可奈何。
也是在这里,在平淡而冷寂的独居中,在热恋与失恋的徘徊与挣扎中,她完成了她自己最精彩的篇章:《倾城之恋》、《沉香屑》、《金锁记》、《心经》……一篇又一篇,篇幅并不太长,却清一色的清贞冷艳,它们成就了她的经典,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经典。
张爱玲在上海公寓里的生活是日常的。她读报纸、买豆腐浆、上下电梯、晚上听着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地流入下意识里去”,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家过日子”的简单事。她爱听“市声”,不是因为它们是舞厅里的时髦音乐,而正因着它们的底层身份,从中不难体味出“小市民”的悲欢离合,人生的无奈和沧桑。如果仔细读张爱玲,你会发现,那些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喧哗,到了张爱玲这里忽然全都偃旗息鼓了,从一个梦幻世界变成了切切实实的人生,虽然这个世界龟缩在以公寓为核心的狭小区域之内。
孤独图书馆:一个人的图书馆,你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我的孤独是一座天堂。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taera.com/krwh/58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