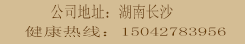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今天不论风月,聊聊张爱玲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今天不论风月,聊聊张爱玲

![]()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今天不论风月,聊聊张爱玲
当前位置: 卡塔尔 > 卡塔尔政治 > 今天不论风月,聊聊张爱玲
编者按:张爱玲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她的文字清冷孤傲,就像她的为人一般,特立独行,成为民国文坛的一抹亮色。她是民国奇女子,她的一生称得上传奇,终其一生,横空出世的来,旁若无人的活,听天由命的走。她笔下的灵魂,文字中的孤傲,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都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余味。
张爱玲
今天是9月30日,96年前的今天,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今天我们不论风月,就聊聊张爱玲。她的文学地位和作品风格已无需赘述,关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已泛滥,然而关于张爱玲在电影方面的贡献和意义却鲜有人提及。今天以一篇极具代表性的文章,来深度剖析张爱玲作为编剧的创作风格,以及其作品渗透的文化身份的焦虑。
注:文章已经由作者授权发布,作者系资深电影史研究学者,对早期电影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犹疑的身份:电懋时期张爱玲编剧影片的叙事特色
黄望莉
提要张爱玲作为编剧,她在20世纪40年代所形成的创作风格也随着她个人生活的变化而带到了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的国语片的创作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南下影人、脱离内地生活的知识分子在延续其海派电影创作风格的同时,其作品中无处不渗透着重塑其文化身份之时的那一份犹疑之情。张爱玲作为一个跨越文学界进入电影创作的剧作者,通观她在两个时期的电影创作均突显出她作者的身影。第一个时期,是在文华影业公司初创期,即年,柯灵因为与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渊源,力荐张爱玲为编剧,创作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第二个时期则是在香港电懋公司制作主任宋淇的推荐下于年开始的新一轮电影剧本创作。香港电懋公司的前身是星马国泰机构在香港设立的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由于永华公司的债务过大,最终被“国泰机构”接手,于年春正式改组为国际电懋公司,陆运涛担任董事长,“永华”的前厂长钟启文为总经理。该公司主要走中产阶级生活和品味,以人情冷暖、男女爱情为主的通俗剧风格路线,出现了生活喜剧片、歌舞片等类型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张爱玲在进军美国文坛失败后,接受了“电懋”编剧主任宋淇的邀请,为该公司编写剧本,以维持她和赖雅的生活,一直延续到老板陆运涛逝世为止。张爱玲这七八年间共编写了十多个电影剧本,投拍的有八部。这些影片是:《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六月新娘》()、《南北一家亲》()、《小儿女》()、《南北喜相逢》()、《一曲难忘》()等。她的另外的几个剧本,如《魂归离恨天》、《红楼梦》(上、下),都因为“电懋”的突发变故而未拍成。这些弥足珍贵的剧本和影片竟成为张爱玲电影创作的绝响。尽管张爱玲创作的剧本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但是她的作品一方面需要面对香港五六十年代商业文化的繁荣,及其在向现代化过渡历程中无法回避的现代性的困境;另一方面,当时大量南下香港的内地影人、投资者、知识分子等,他们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感和文化依赖都投射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因此,纠结在张爱玲所编写的八部影片中所突显的女性情感的不确定性、叙事空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家庭伦理叙事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也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当时香港南下影人们的流离感和自我身份归属的困境。
《太太万岁》()
一、《情场如战场》:回归家庭的犹疑张爱玲早在40年代后期的两部影片《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都大量地借鉴了好莱坞神经喜剧(ScrewballComedy)的叙事观念,与此相呼应,5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电影剧本创作依然延续了这一创作风格。例如,为了追求“高乘喜剧”在知性层面上的诉求,张爱玲这个时期的影片也同样大量地依靠对白,针对人性的弱点和可笑的一面加以善意的嘲讽,尤其是在女性形象的建构上更突显其复杂性。例如,张氏电影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不仅仅是作为男性的对立面来展现的,更多的是纠结于女性自身的不可捉摸性,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行为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情场如战场》中的“叶纬芳”摇摆在三个男性中间,无法明确究竟她爱的是谁?《人财两得》中的两任妻子对男主人公的争夺,一度自己也糊涂了,弄不清自己究竟是离婚了,还是未离婚。两个妻子就像一个女性的两面,来指代女性难以自我归属、自我确认的困境。自从年“电懋”接过“永华”后,邀请了大量有着上海文化背景的文人成立“剧本编审委员会”,其中包括:姚克、孙晋三、张爱玲、宋淇等,当时宋淇担起主导大权。张爱玲被引入的主要原因还是看重她在上海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华”阶段的电影剧本创作的成功。果然,影片《情场如战场》是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影片公司写的第一个剧本,由于该部影片延续了上海“趣剧”电影风格而大受欢迎,直至今日,亦被誉为香港百部名片之一。虽然影片《情场如战场》改编自美国舞台剧《温柔的陷阱》,然而却鲜明地打上了“张氏”的印记。故事写的是一对姐妹对待爱情的两种做法,姐姐保守胆怯,妹妹活泼奔放,而且妹妹是以征服每一个男性为乐,尽管这个男性是姐姐喜欢的,她也要施展魅力给夺过来。这个情场不仅仅是异性之间的战场,也是同性之间的战场。毫无疑问,这部影片充分调动了张爱玲描写女性的妙手展现其一贯的叙事母题:“两性关系的角力”。简单来看,《情场如战场》采用的是“一女三男”的叙事模式,这部影片极端之处就在于林黛所饰演的叶纬芳的角色,在两性角力的书写过程中,张爱玲显然并无贬损女性的意思,反倒是大量地展现女性智慧,哪怕是恶作剧,哪怕是丧失一点点道德感都无关紧要。叶纬芳娇媚中暗暗地捉弄着他人、任性中淋漓尽致地享受着青春,无时无刻不泼溅出生命的活力。叶纬芳这样的女性通过自身的智慧就可以尽情享受着人生追逐的游戏。相比较40年代《太太万岁》中的施咪咪形象的塑造,叶纬芳变成了大家闺秀,并成为故事的主角,女性对男性的操纵不再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十年之后,在张爱玲的笔下变得张扬而大胆,甚至与男性展开了面对面的挑战。如叶纬芳的表哥史榕生明知道叶纬芳“心眼太活,虚荣心又大,恨不得普天下的男人都来追求她。谁要是跟她认真,那可准得受很大的刺激”。可是,当叶纬芳出乎意料地宣布她真正爱的是表哥史榕生的时候,史榕生却选择落荒而逃,最后故事以表哥无处可逃作为结局。
《太太万岁》()
在张爱玲两性角逐的叙事中,女性似乎一直能够超越男性,成为胜利者,然而,仔细看来,女性其实一直处于不确定自己感情归属的困境中。叶纬芳在故事的大半个部分中一直游离在白领陶文炳和教授何启华之间,无法也无意于做出抉择,最后,即使看似选择了表哥史榕生,可是故事最后还是没有明确女主人公的真正归属,依然给观众留下了悬念。此时,在张爱玲的叙事中,女性是一个飘荡的主体,希望寻找婚姻家庭的归属,而男性的恐惧、张皇和不稳定性使得女性只能游戏其间,毫无归属感。这种感受在《六月新娘》、《桃花运》中也不断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六月新娘》中汪丹林的“逃跑”是因为怀疑未婚夫与其他女性有关系,而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疑惑。尽管最后结婚了事,但是其疑虑依然未解;《桃花运》里的太太瑞菁就像《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聪慧而且敏感,面对不堪的丈夫,一度游离出了家庭,尽管最终通过自己的智慧将一个即将破裂的家重新又赢回来。可见,婚姻/家庭/男性作为男权社会中女性必然的归属之地在此时张爱玲的笔下受到质疑。表面上看来这代表了香港50年代后期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女性解放后对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重新思考,然而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女性所处的当时广泛的现实(内地与香港和台湾隔离,香港的殖民政治,台湾的独裁政治等)才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难以获得归属感的真正原因。从张爱玲一生的命运来看,她就像一个无根的浮萍,根本就是一个漂泊者,离开上海到过日本,再从日本辗转香港,到了美国也不断地在搬家,正如一篇关于她的评传中描述到:“她最后几年住的房子,除了一张窄窄的行军床、电视机、落地灯和一张折叠椅及一把折叠梯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她刻意过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一方面是便利迁移,一方面也是对过往贵族生活的扬弃吧。”或许,便于搬迁的居家生活可能是她这种居住环境选择的最主要的因素吧。两次的婚姻不幸和最终流落异乡为异客的感受无论如何也难以让张爱玲写出具有归属感的故事,40年代所热衷于对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脚下“袅袅升起的炊烟”之感早已荡然无存。事实上,张爱玲的飘零感、无家感已经融于她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了。张爱玲对女性所处困境的描写穿越影像文本投射为社会文本,形象地描摹出五六十年代香港自身归属的不确定性。
《情场如战场》()
二、《南北一家亲》:上海意识VS香港身份张爱玲年离开香港后,虽然身在美国,但是美国出版界对她的排斥使得她只是异乡的客居者,60年代的台湾之行也难以让她认同,只有到了香港,这个既有着当年上海的都市气质,又游离在政治之外的地方,能够让她获得些微的共鸣。在她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仍然着力于对香港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像当年她所描写的上海,在她的笔下经常会交融在一起,上海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又交织在她当时的剧本中。以至于她笔下的香港都市空间也显得空泛、模糊不清。其实,张爱玲剧本从取材到故事戏剧核心冲突的构建,再到叙事文化的呈现上都有着突出的跨地性特点。首先,在取材上多是从国内外的电影、戏剧改编而来的,如《情场如战场》取材自美国舞台剧《温柔的陷阱》,《一曲难忘》取材于好莱坞名片《魂断蓝桥》,影片《小儿女》被誉为40年代张爱玲的合作者桑弧编导的名片《哀乐中年》的香港版。而《六月新娘》则由好莱坞的“逃跑新娘”的故事原型改编而成的。《南北喜相逢》改编英国话剧《真假姑母》等。南来影人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拍摄过程中,依然保留并延续着上海电影传统,在制作上看似西化的拼贴,似乎与上海无关,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上海影人是一贯西化的,例如,文华影业公司在40年代对好莱坞“神经喜剧”的模仿,形成了自己的影片风格和“趣剧”的电影形态。张爱玲恰恰就是连接起上海—香港“趣剧”电影传统的纽带式人物。在核心叙事冲突的建构上,电懋公司的“南北”系列喜剧在当时香港电影中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从《南北和》()、《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到《南北喜相逢》()等,故事以大家庭为核心,讲述五六十年代存在于香港的地域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南北两家人互相斗气、由冤家最后皆大欢喜变为亲家的故事。纵观“南北”系列喜剧的形成过程,第一部影片《南北和》原是宋淇在“电懋”的新春慈善联欢会上演出的一个独幕剧发展而成的,而后两部影片虽是由张爱玲编剧的,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南北一家亲》原署名为“秦亦孚”,后由张爱玲改编而成的。而“秦亦孚”即为香港著名影星、翻译、编剧“秦羽”,也是“赵四风流朱五狂”中的北洋名媛“朱五”的女儿。可见,从宋淇到张爱玲再到秦羽,“南北”系列的根基还是在于这群由北方/内地到香港的影人。他们对南北文化差异的感同身受,以至于“南北”系列获得那个时代的回应。该系列片不仅在香港,而且在台湾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电懋”的老对手“邵氏”也立刻跟进《南北姻缘》,连台湾都抢拍汉语普通话和闽南语抬杠的《宜室宜家》。由于当时香港主体电影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大量的跨地性的特质,因此,在其影像的呈现上也使得香港本土的身影变得模糊不堪,相反,多地性的文化特征在此却彰显出来。因此,这些看似温情的影片却不断地纠结于这种“南来的委屈”感,即不被认同、也难于自我认同的情绪矛盾中。张爱玲、秦羽和宋淇等人在这一点上都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感受。“南北”系列影片多是命题作文,但在总体表述上还是显得较为一致。“南北”系列喜剧片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它很能代表20世纪60年代港人的情结。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电懋公司“多半影人来自上海,在心态上不脱中国意识”,其三,在叙事文化的呈现上,张爱玲电影也显示出多元性。例如,《六月新娘》的故事看上去是发生在香港,可是仔细想来,故事其实发生在哪里都可以,可以是上海,也可以是台北,更可以是美国,该故事的人物背景也较为复杂,有从日本回来安排准备结婚的父女,也有从轮船上回港娶妻的水手,夜总会的舞女,完全西洋化的乐人,而寻其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的家族背景还是一群从上海流亡到国外的经商世家,故事的时代背景被置于60年代的香港,更唤起当时漂流在海外华人的感情共鸣。与《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中一样,50年代张爱玲在“电懋”开始创作的影片中也大量充斥了都市生活景观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展现。《情场如战场》的主场景叶家的郊外别墅景点借用的是香港名门余东璇的浅水湾别墅内拍摄的,更别说充斥着汽车、泳池、化装舞会等生活内容和场景,这些显然脱离当时香港中产阶级真实的生活内容,因此,也备受一些批评家的诟病。其实,张爱玲一直热衷于对香港上海等地现代都市生活的展现,而此时香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已经在张扬自身的西化生活方式了。宋淇编写的《南北和》虽是“南北”系列中的第一部,相比较于张爱玲随后同系列的作品,影片的节奏轻盈却不紧凑,笑料也仅限于误会、斗气,诸如台词“你说四大美女哪一个是南方人?”这类斗嘴的笑料,有硬性拼贴的感受。而到了张爱玲的《南北一家亲》中,她所使用的笑料则淡淡地、不着痕迹地出现在人物表现和整个生活叙事逻辑之中,微妙而细腻地展现出她对南北文化的差异的切身性的感受。例如,她在李曼玲到张清文家里去见排斥“北方人”的公婆那场戏里,张爱玲就设计了一个做萝卜糕的悬念;随后一场戏是两个人化险为夷后讨论去见李曼玲自己父母的时候,李曼玲纠正张清文的发音,“日头、石头、舌头”,在张清文的广东口音中则成了“易头、习头、鞋头”,令人忍俊不禁。可见,张爱玲将这些笑料巧妙地运用到了影片日常化叙事的表述中。香港的身份,上海的意识,这些混杂的现实使得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南来知识分子难以在当时获得明确的国族和文化身份,也只有通过“通俗剧”置换其家国情怀。
《南北一家亲》()
三、《小儿女》:家族的情怀通俗喜剧电影模式是“电懋”电影创作的一个流向。《小儿女》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继承好莱坞“通俗剧”类型的影片,也是张爱玲编写的十部影片中最为独特的一部。正如前文所述,很多论者都非常补骨脂注射液副作用白癜风要注意什么转载请注明:http://www.nanjizeiouz.com/krzz/226.html